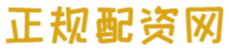在预算制度改革方面,《决定》提出了七大主要任务:
党项拓跋氏首领拓跋思恭借着黄巢起义,掌握夏、绥等州,号为“定难军节度”,成为唐末藩镇之一,割据一方。定难军节度便是后来西夏政权的前身。
五代的党项诸部,虽然处于不相统一的状况,但以“大姓之强者”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几个较大的割据政权。其中包括有唐末以来盘踞夏、绥、银、宥四州的党项拓跋氏,五代兴起于府、麟二州的党项折氏和处居于庆、灵二州之间的西路党项这三个较大的党项集团。
宋辽长达四十余年的战争,使得扎根于宋辽夹缝之间的党项部族得以迅速茁壮成长。宋太宗执政至真宗景德元年这数十年中,宋廷因与契丹的战争,无力大举兴讨西北党项部族。
与此同时,党项又获得了来自契丹的经济及军事上的支援。从另一个方面看,契丹采取“以党项制宋”的策略,着力于扶持党项的成长,又使宋廷不得不分兵西北,无法全力经略幽燕。
其实在赵匡胤时代,党项人与宋廷的关系还是比较良好的。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即皇帝位,此时的定难军政权奉表称臣,但定难军政权实际上依然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
当时北汉主刘钧曾结契丹寇麟府。党项李彝殷欲沿袭五代以来与邻近政权的表面依附关系,便遣部将李彝玉出兵增援麟州;并以避宋太祖之父赵弘股之讳为由,改名李彝兴,表示归附。
建隆初,李彝兴遭使献马300匹。宋太祖大喜,亲自挑选玉材,准备为他制作一条王带。制作时,宋太祖亲自召来党项使者询问李彝兴的腰围。在得到了李彝兴腰围较大的答复后,宋太祖对使者说道:“这帅真福人也。”并让使者将玉带交予李彝兴。
乾德五年(967年),李彝兴辞世。同年十二月,李彝兴之子李光睿继承定难军节度使之职。及至开宝九年(976年),宋廷兴兵伐北汉时,李光睿还曾出兵帮助宋军。
李光睿“率兵破北汉吴堡寨(今陕西吴堡),斩首七百级,获牛羊干计,俘寨主侯遇以献,累加检校太尉”。同年,宋太祖赵匡胤病死,宋太宗赵光义即位。李光睿因避太宗名讳,改名李克睿。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李克睿卒,太宗以其子李继筠为权知州,并授以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太宗征北汉,李继筠遣银州刺史李光远、绥州制史李光宪率兵列阵渡河,以张军势。七月,李继筠病死。
太平兴国五年,宋廷以其弟李继捧为定难军留守。然而就在李继捧继任后不久,夏州李氏便发生了内部分裂。同时,北汉、南唐等诸割据势力先后告平,宋大宗有意谋取定难军政权,将夏、绥等四州之版图收归宋朝。从此后,党项人与宋廷的关系开始走向决裂。
太平兴国七年,李继捧入朝面圣,自述其即位引起其叔伯的不满,因而愿请留京师,并献上所管四州八县。李继捧入朝,成为李继迁揭起反旗及掌握定难军政权、与宋廷公开决裂的契机。
太平兴国七年十一月,太宗诏李继捧的叔伯李克宪、李克文赴阙,并以李克文权知夏州。其后,宋太宗以曹光实为银、夏、绥、麟、府、丰、宥州都巡检使,以期扼制夏州李氏的势力。不过,宋太宗此举常常被一些学者批判。
确实,夏州李氏自唐末以来长期割据一方,势力盘根错节,要削弱党项在西北的势力,以避免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乱局,李继捧入朝寻求宋廷帮助平定内乱,恐怕是当时最好的机会了。
宋廷上下深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道理,但该举措却严重低估了党项在西北的势力以及李氏在夏州百年的经营。
雍熙元年,宋太宗诏李继捧亲属赴阙。诏令到达银州之时,李继捧族弟李继迁因不服宋廷统治,玩了招暗渡陈仓。他先诈称乳母过世,出葬于郊外,又将兵器及甲胄藏于棺中,带着数十人马逃遁。
逃入地斤泽的李继迁随后拿出先祖李彝兴之画像示党项众人,“戎人皆拜泣”。然后他又扯出李彝兴的大旗说道:“李氏子孙当以恢复祖宗遗业为志”,以此煽动党项部族的反抗情绪。
同年九月,时知夏州尹宪侦知李继迁藏身于地斤泽,便与曹光实趁夜发兵。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李继迁仅单身逃脱。
但是李继迁显然不会甘心。什么都没有的他,只能依靠祖宗的大旗来获得支援。于是,李继迁便与诸藩豪酋联结姻亲,以扩张势力,并继续煽动、联合党项诸部。
雍熙二年(985年)二月,李继迁诈降。曹光实欲独占功劳,又认为李继迁的势力在地斤泽之时已经被消灭,于是当李继迁遣数十骑进城迎接曹光实时,曹光实信以为真,仅带数百骑深入敌营,结果为李继迁设伏诛杀。
其后,李继迁占据银州,并自称“定难军留后”,继续扯祖宗大旗,次月又破会州(今甘肃靖远)。从这个细节可以知道,当时宋廷上下对党顶人普遍有一种俯视的态度。
这种俯视往往来源于以往的军事斗争中宋军的胜利,但这种态度却间接导致了胜利后紧随而来的失败。可悲的是,在宋与党项的斗争中,往往重复着这种“胜利后骄傲,骄傲后失败,失败后谦虚,谦虚后又胜利”的循环。
曹光实身死使得宋太宗大怒,随即派遣田仁朗、王侁及李继隆发兵数千剿灭李继迁。田仁朗到了绥州之后发现,叛军规模已然扩大,凭手中兵力不足以镇压李继迁势力,于是上奏请求援兵,并按兵月余不动,等待朝廷回复。
其间,原本归降于宋廷的党项三族寨将领折遇也谋杀监军使者,与李继迁合兵。宋太宗为王侁误导,以田仁朗按兵不动、延误军机,改遭刘文裕取田仁朗而代之。
同时,宋廷又遣王侁从银州北出兵,于浊轮川大败李继迁。郭守文又与尹宪合击盐城诸夏部族,银、麟、夏三州及三族寨,党项诸部百二十五族纷纷内附。
因此,李继迁叛宋以来节节败退。在此种情况下,李继迁采取了联辽抗宋的措施,希冀宋廷之大敌契丹可以给予其援助。他于雍熙三年二月遣使向辽称臣。十二月,李继迁向契丹请婚。
契丹以义成公主下嫁,并赠马3000匹。得到契丹的大力支持后,李继迁卷土重来,不断寇扰夏、银诸州。宋廷多次以敕书招谕李继迁及同恶蕃部,而李继迁也曾自陈有依附宋廷之意,但始终不肯归降,并“益侵盗边境”。
端拱元年五月,宰相赵普建议以夏台故地赐予李继捧作为诱饵,伺机谋取李继迁。太宗听从了这个建议,赐李继棒国姓赵,改名保忠,并授予定难节度使,将所属夏、银、绥、宥、静五州钱帛、粮草及田园赐还赵保忠(即李继捧)。
同年十二月,赵保忠奏曰继迁归降,并“诱藩入寇,乞师守御”。宋廷以为一旦犹疑,恐生变故,于是在未察之下匆匆授予李继迁银州刺史、洛苑使。但此时李继迁并未真正归降,而是与赵保忠勾结瞒宋。
暗通李继迁的赵保忠,于端拱二年及淳化元年(990年)又奏李继迁数次得建边功,以麻痹宋廷,为李继迁招兵买马、扩大势力、训练精兵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十月,李继迁在经过了数年精心准备之后,率兵攻打夏州,并大败宋军。赵保忠上表乞援,而李继迁随即向辽告捷。
淳化二年(991年),宋朝遣翟守素出兵援夏州。此时,李继迁再次诈降,宋廷授继迁为银州防御使及绥州观察使,并赐李继迁姓名赵保吉。结果就这样,李继迁一边玩弄宋廷,一边兵不血刃地取得了银、绥两州。
李继迁之所以可以在出逃之后,迅速地建立起相当的势力,是有其内在因素的:
其一,宋与契丹此时正处于不断的交战之中,宋廷难以全力讨伐西北党项,而契丹也欲以党项牵制宋军,因此不断对党项进行支援;
其二,从曹光实剿灭地斤泽的党项部族,到他被李继迁设伏杀死,只间隔短短五个月的时间,这显然可以反映出当时西北地区反宋势力的强大;
其三,五代末以来,党项诸部只剩夏州拓跋氏一支独大,其他两支较大的势力已然衰落,党项部族长期群龙无首,对于此时站出来的李继迁自然多有响应。
而宋太宗对李继迁之放任,究其原因,一来因契丹的不断侵扰而无力发兵西北;二来宋太宗还打着“以藩治藩”的如意算盘,意图将平夏李氏这颗钉子安插在西北地区,以增强宋廷对西北的掌控力,乃至于凭此图谋幽燕;三来,此时的宋廷统治者依然轻视党项问题,并没有看到李继迁反叛可能引起遍布西北的所有党项部族的反叛。
当时的西北地区,除去分散的党项一支以外,较为强大的还有回鹘诸部与吐蕃诸部。尽管吐蕃与回鹘均曾数事宋廷,但这只不过是他们实力较弱时的选择罢了。
吐蕃之先祖松赞干布曾一统西北,且正如宋真宗在咸平二年所说,“肤看《盟会图》,颇记吐蕃反覆狼子野心之事”。可见宋廷的统治者对吐蕃实则怀有戒心,其对西北的主要担忧,也是在曾经一度攻克唐都长安的吐蕃身上。
回鹘虽看似对宋忠心耿耿,实则更可能是欲借宋廷之力开疆拓土,也暗表其实力雄大,略有警诫宋廷“莫轻易招惹于我”之意。何况有归义军为西北诸羌侵略在前,宋廷怎能不对回鹘有所防备?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考虑,宋廷便欲放任夏州李氏,以制衡吐蕃与回鹘。于是淳化二年李继迁诈降之时,宋廷未加思索便信以为真。但当平夏李氏势力过大,抑或脱离掌控之时,宋廷则会加以打压,使其顺服。
当然,宋廷的政策也有其局限性。其一,北宋西北地区被回鹘、吐蕃及党项割据,所以宋廷对西北的掌控力极其有限;其二,这种掌控力的局限性,使得北宋消息闭塞,难以及时了解西北地区的政治形势和各势力的消长;其三,宋廷依然低估了党项,尤其是平夏李氏的势力及反宋之决心。
党项在西北盘踞多年,除去占据夏、银、绥、宥、静五州的平夏李氏,尚有灵、武、瓜、凉州等也被党项及其他西北部族共同占据。乃至于陇右之远,也依然有党项部族定居。这才使得李继迁有振臂一呼、诸羌景从的客观条件。
而且,宋廷这种养虎为患的例子,在历史上也并非是绝无仅有的。如明末,李成梁意图以努尔哈赤制约辽东各女真部族,结果努尔哈赤在李成梁的支持下统一了辽东女真各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后金。
淳化二年李继迁归降于辽后,又继续策反赵保忠(即李继捧)归顺。见夏州李氏势力不断扩大且游于掌控之外,赵保忠之叛心亦与日愈昭。宋太宗遂于淳化三年(992年)禁党项青白盐市,希望凭借经济制裁,削弱李继迁势力,并使其归附。
党项诸部原以贩卖青白盐获取粮、资,因而,此举可谓切中要害。令行数月,不仅平夏李氏,就连夏州左近的党项诸部也因经济困难而难以维生。
此时,不仅平夏李氏,乃至于原本降宋的党项部族也开始反叛。李继迁趁乱于淳化四年(993年)攻打庆州及原州(今宁夏固原)。同年,太宗见青白盐禁不仅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甚至造成原本归顺的诸党项部族叛逆,又匆匆取消了这一禁令。
淳化五年(994年),李继迁又取得灵、庆党项诸部的支持,遂转攻灵、庆二州及清远军(今宁夏盐池)。宋太宗大怒,命马步都指挥使李继隆为河西兵马都部署、尚食使“黑面大王”尹继伦为都监,率军征讨党项。此为第一次讨伐。
此时身在夏州的定难军节度使赵保忠却又诈称李继迁想和解。其实,此时的赵保忠反心已昭。上当好几次的宋太宗知道这又是党项的诈降计策,对此不予理会。
是年三月,李继隆所率宋军败藩兵数千于石堡寨(今陕西靖边)。时赵保忠在城外,李继迁以为赵保忠向宋廷通风报信,于是率兵攻打。
里外不是人的赵保忠只身逃入夏州城中,为大将赵光嗣囚于别室,其后被押解入朝,太宗封其为“宥罪侯”,赐第京师。
同年六月,李继迁再次诈降,其后遣派其弟李延信赴京师上表请罪,并言反叛之事为赵保忠所策。宋太宗召见了李延信,对其进行抚慰,并加以赏赐。
至道二年(996年),宋洛苑使白守荣护送刍粟40万石前往灵州。行至清远军时,白守荣为李继迁所袭,刍粟皆为李继迁所掠。
这标志着李继迁已与当地党项诸部联合,控制了宋朝由环庆至灵州的交通要道。由于宋廷对西北局势的掌握太弱,消息闭塞。直至此时才发觉,夏州李氏已“据平夏全壤,扼瀚海要冲”,势力已远超宋廷的想象。
于是,当年四月,宋太宗以李继隆讨伐李继迁。至五月,李继迁率兵万余围攻灵州城,为窦神宝击退,但粮道已断,灵州孤绝,情况依然不容乐观。因此,宋太宗令宰相吕端等献策解灵州之困,甚至想过是否应该放弃灵州。
时参知政事张洎上奏曰:“继迁或成或败,未足致邦国之安危;灵武或存或亡,岂能系边陲之轻重?得失大较,理甚阳然。”
又言即便眼前危机解除了,但一来灵州凋敝,难以坚守;二来灵州不能自给,需“驱秦、雍之百姓,供灵武之一方”,不如放弃。
宋太宗此时早已打消了放弃灵州的念头,读到张泊的奏章时心有不悦,便责备张洎说:“卿所陈,朕不晓一句!”
同年九月,宋太宗以李继隆自环州(今甘肃庆阳环县),范廷召自延州,王超自夏州,丁罕自庆州,张守恩自麟州,共五路大军出兵至乌、白池(今宁夏盐池县北内蒙古境之北大池一带)会师,并“皆先授以方略”,以解灵州之围。
五路军主力李继隆一军原本应赴乌、白池,与其他四路宋军会合解灵州之围。然而银、夏铃辖卢斌对李继隆说:“由灵州趋乌、白池,月余方至,若自环州抵贼巢,才十日程尔。”
李继隆贪功冒进,听罢之后未有请示,自作主张地率大军直趋平夏,然后派遭其弟李继和上言说:“赤柽路回远乏水,请自青冈峡(亦作青冈岭,今甘肃环县西北)直抵继迁巢穴,不及援灵州。”
这一典型的先斩后奏行为触怒了宋太宗,于是他召来李继隆的弟弟李继和骂道:“汝兄如此,必败吾事矣!”
李继隆自环州出兵平夏,遇见自庆州而出的丁罕一军,便与丁罕合兵,从青冈峡出发,前往李继迁巢穴。然而他们“行十数日不见敌,引军还”。
自麟州所出的张守恩一军在途中遇见李继迁的军队,因未会合主力而不敢与敌军交战,归还本部。仅范廷召和王超两军到达乌、白盐池会师,并击败李继迁所部,且“多有俘获”。
但因为丁罕、张守恩及主力李继隆三军失期,宋军虽有小胜,却未能取得关键性的胜利,也未能成功削弱平夏李氏之势力,第二次西讨党项最终也功败垂成。
不过,并不能将“二伐党项”失败的责任全部扣在李继隆的头上。毕竟从李继隆与丁罕的匆忙退军,其实可以看出宋军所暴露的补给问题。
至道三年(997年)三月,宋太宗欲第三次出兵平夏解灵州之围。结果虽然粮草已至,宋太宗本人却病卒,第三次西讨党项未能成行。
终宋太宗一世,共计三次兴大军西伐党项。第一次因李继迁诈降而收兵,第二次因李继隆擅改战略目标而功败垂成,第三次因太宗病逝无疾而终。
夏州李氏自唐末后据有夏、绥、银、宥四州,而这四州均处鄂尔多斯高原南部地区。党项立西夏国之时,其足迹已遍布河套地区。
当时党项所居之地有大大小小的湖泊分布,这正是夏州拓跋氏赖以发展的源地。前文所提到的地斤泽,便是众多湖泊当中的一处。尽管不可过分高估其生态环境,但这些湖沼显然是党项部族赖以繁衍的基础所在。
在党项部落掌握湖泊水源的同时,西北地区的沙漠化日趋严重。唐长庆二年(822年),已有“飞沙为堆,高及城堞”的景象。至唐中后期时,此地已然有严重的沙漠化现象。
河套乌兰布沙漠形成较早,于东汉至南北朝间不断扩大;而在鄂尔多斯南部的毛乌素沙漠形成于唐代末至五代初;库布齐沙漠则形成于清末到民国初年。
原来赫连勃勃所说“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之地,至宋时已经变成瀚海沙漠戈壁700里。河套地区的广袤沙漠,成为以步兵为主的军宋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
故而曾布才说:“朝廷出师,常为西人所困者,以出界便入沙漠之地,七八程乃至灵州,既无水草,又无人烟,未及见敌,我师已困矣。”
众所周知,后勤在战争中尤为重要。这种沙漠化,不仅仅造成了宋军行军的困难,也使宋军的后勤遭到严重的威胁。
实际上困于沙漠的并不只赵宋一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霍去病、卫青所率汉军大败匈奴,但“汉两将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物故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匹。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
可见汉代之时,戈壁已困扰汉军,成为当时匈奴所依仗的天然壁垒。显然,若无强大的骑兵与后勤,单靠步兵不足以横穿荒漠,后勤亦不能得到保障。
在历代战争中,粮食供给的最主要方式有二,一是运输,二是屯田。屯田虽然耗费较小,但经营却旷日持久,难以即时收效。因而,北宋早期西北战场的粮食补给,依然是以运输为主的。
当时,距离宋朝西北战场最近的农业发达区是关中平原,但二者距离仍在300公里以上。显然,这个距离对于粮运来说并不短,人力、物力所耗必然甚大。
在运输上,“一夫雇直约三十千以上,一驴约八千”,而且“凡费粮七万余石,钱万有余贯,才得粮二十一万石,道路吁嗟,谓之地狱”。
有时如果距离太大,运输之费还会多于运输之物本身所值,甚至是数倍之多。“绛州运枣千石往鳞府,每石止直四百,而雇直乃约费三十千”。因而“岁费浩大,支计不充。百姓困于供输,有司疲于漕饷”
宋廷为第三次西伐党项做准备时,就“竭内帑之财,罄关中之力”。西北地处荒凉,难以自给,加之运输所费甚大,对于宋廷而言是极大的负担。
因而,张洎在劝宋太宗弃灵州之时上奏所言“驱秦、雍之百姓,供灵武之一方。使无辜之民,膏涂原野。朝廷大计,岂若是乎”,便是出于此番考虑。
若是长期以粮运进行供给,宋廷必然不堪重负。而且所输运的粮食还可能被敌军的劫掠。故对于宋廷来说,在西北战场进行屯田是必然的选择。于是在宋真宗以后,北宋便在西北战场修建堡寨,并进行大规模的屯田。
屯田并非西北战场之独创。远至汉唐,乃至于宋辽战争中,屯田都是军队粮食补给的重要来源。不过其负面因素前面也说了,修建堡寨费时费力,屯田又需长期经营,都很难在短时间内见效。
加之自宋太宗雍熙元年之后,西北烽烟才逐渐燃起。而至淳化年间,平夏李氏都未引起宋太宗太多的重视,反而希冀可凭借党项部族牵制回鹘与吐蕃。
党项诸部真正引起宋太宗的重视并进行大规模征讨,已经是至道年间的事了。至于堡寨与屯田的兴起,则在宋真宗以后。这就更凸显了屯田的负面因素。
特别要说的是,屯田的本质是在前线地区经营农业,那么就必然受当地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所制约。正如之前所考证的,及至北宋之时,西北地区沙漠化情况已然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北宋西北战区的屯田分布及收益也受到很大局限。
另外,党项作为游牧民族,其作业方式与汉族有很大差异。在宋初之时,党项的经济模式依然是以牧业或半农半牧为主。牧业(尤其是游牧)对地理、气候条件的要求与种植业是完全不同的。
平夏地区绿洲肥美,党项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也通过打草谷等方式获得粮食补给。但宋军则完全不同,只能通过绵长的运输线对粮食进行转运。
宋朝因畜牧业不发达和河套地区沙漠化日趋严重,造成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缺乏强大的骑兵,700里瀚海对于宋廷来说犹如天堑;二是机动性差,在战争中受到的制约太大;三是补给困难,不仅是屯田的地域收益受到严重限制,在运输上也造成很大困难。
并且,在当时,宋辽之间还处于全面战争之中。所以股指配资平台,只有彻底忽略北宋在西北的战略意图,以及宋代马政及补给困难、所费兹大等问题,才能硬说因为军事失败主义抬头,加之强干弱枝、重文轻武,北来朝廷上下不敢兴讨西北党项诸部,而仅以羁繁、绥靖苟求安宁。
发布于:天津市